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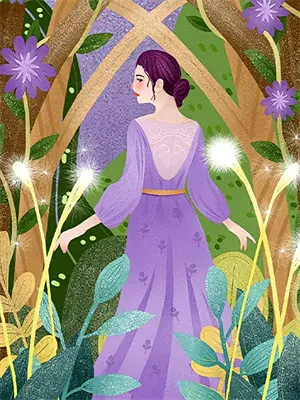
言情小说连载
言情小说《枇杷黄到什么时候采摘讲述主角枇杷陶乐瑶的甜蜜故作者“青椒黄瓜小番茄”倾心编著主要讲述的是:1 福气小胖妞我胎穿成江南农家小胖绑了个叫博闻馆的啰嗦系阿娘愁我吃太隔壁婶子笑我圆只有村口小乞丐会偷偷给我塞野乐给!他拿着最大最黄的枇乐甜!他黑瘦的手心躺着红透的野五年我把改良的枇杷膏卖到了州他带着一身伤疤和几个同样风霜的兄弟站在我家院曾经的小乞丐成了总却在我面前红了耳根五岁的陶乐瑶坐在自家门槛对着春日暖融融的太慢吞吞地啃着一...
主角:枇杷,陶乐瑶 更新:2025-09-28 01:10:18
扫描二维码手机上阅读
1 福气小胖妞我胎穿成江南农家小胖妞,绑了个叫"博闻馆"的啰嗦系统。
阿娘愁我吃太多,隔壁婶子笑我圆润,只有村口小乞丐会偷偷给我塞野果。"乐瑶,给!
"他拿着最大最黄的枇杷。"乐瑶,甜!"他黑瘦的手心躺着红透的野莓。五年后,
我把改良的枇杷膏卖到了州城,他带着一身伤疤和几个同样风霜的兄弟站在我家院外。
曾经的小乞丐成了总旗,却在我面前红了耳根五岁的陶乐瑶坐在自家门槛上,
对着春日暖融融的太阳,慢吞吞地啃着一块硬邦邦的杂粮饼子。饼子剌嗓子,她小眉头皱着,
努力用刚长齐的米牙磨。阿娘赵金花端着木盆从灶房出来,瞧见她这费劲模样,
又是心疼又是无奈地叹气:“我的小乐瑶哟,慢些吃,又没人跟你抢!哎,你说你,
咋就这么能装饭呢?”她放下盆,粗糙的手指爱怜地戳了戳女儿圆鼓鼓、白里透红的脸蛋,
那手感软弹得紧,“瞧瞧,咱家米缸都快叫你吃空啦!”隔壁王婶子正挎着篮子经过,
闻言探过头来,瞅着陶乐瑶那张粉团子似的圆脸和胖乎乎、藕节似的小胳膊小腿,
顿时乐开了花,嗓门敞亮:“哎哟金花!瞧你这话说的!咱乐瑶这福气身子,多招人疼!
圆滚滚的,跟年画上的胖娃娃一个样儿!这叫有福!你愁个啥?”她说着,
顺手从篮子里摸出个小小的、蔫巴巴的野梨子,塞进陶乐瑶另一只空着的小手里,“来,
乐瑶,婶子这儿有个果子,给你甜甜嘴儿!”陶乐瑶抬起小脸,
对着王婶子露出一个甜甜的笑,脸颊上两个小梨涡深深陷下去:“谢谢婶子!”声音糯糯的。
她低头看着手里这又小又丑的野梨,脑子里却不受控制地“叮”了一声。
眼前瞬间展开一片旁人看不见的、柔和的光幕,
上面几行端正的小字浮现出来:识别:野梨Pyrus calleryana,
蔷薇科梨属。状态:轻微脱水,表皮有擦伤,部分组织开始褐变,糖分有所流失。
可食用部分分析:果肉占比约73%,水分含量约82%,
剩余糖类主要为果糖、葡萄糖约8.5%,有机酸苹果酸、柠檬酸为主约0.4%,
维生素C含量较低约3mg/100g,
膳食纤维约2.1g/100g…建议:去皮食用,口感酸涩微甜,粗纤维较多。
陶乐瑶默默啃了一口手里硬饼子,压下心底那点翻腾的复杂滋味。这玩意儿叫“博闻馆”,
在她刚在这个名叫周家坞的小村子、周木匠家落地的头一天,就跟着她一起来了。
像个甩不掉的、过分博学的老学究,看啥都要给她分析个底朝天。她一个胎穿的现代灵魂,
被困在这五岁小胖妞的身体里,还得天天听这“馆”唠叨她吃了多少碳水、多少粗纤维。
日子过得…着实有点魔幻。她爹陶大壮是个手艺还过得去的木匠,老实巴交,
整天跟木头刨花打交道。阿娘赵金花爽利能干,操持家务、伺弄菜园都是一把好手。
上头还有个哥哥陶立安,今年十岁,已经在镇上的李秀才开的蒙学堂念了两年书,
是家里最大的指望。日子清贫,但爹娘慈爱,哥哥也护着她,邻里乡亲大多和善,
像王婶子这样爱打趣她两句的,也绝无恶意。这开局,不算顶坏。
只是这“博闻馆”…陶乐瑶又咬了一口饼子,用力嚼着,仿佛在跟这穿越的机遇较劲。
“乐瑶!发啥呆呢?”哥哥陶立安清亮的声音从屋里传来。他刚下学回来,洗了手,
脸上带着读书人特有的斯文气,手里拿着本薄薄的《千字文》走过来,挨着妹妹坐在门槛上,
“来,跟哥认字儿。昨天教你的‘天地玄黄’,还记得不?
”陶乐瑶立刻把杂粮饼子和脑子里乱飞的营养分析甩开,仰起小胖脸,
脆生生地念:“天地玄黄!”声音又响又亮。“宇宙洪荒!”陶立安满意地点头,
指着书上的字,“看,这是‘宇’,这是‘宙’…”阳光暖融融地照在兄妹俩身上,
陶立安清朗的读书声和陶乐瑶稚嫩的跟读声混在一起,飘出院墙。
阿娘赵金花在院子里晾衣裳,听着这声音,脸上笑开了花,
方才那点对米缸的担忧也暂时抛开了。日子嘛,紧巴是紧巴点,可有儿有女,平平安安,
比啥都强。2 枇杷情缘日子像村边那条清浅的小溪,不紧不慢地淌着。
陶乐瑶在“博闻馆”事无巨细的分析和阿哥陶立安有意无意的教导下,认字飞快,
对周遭草木鸟兽、五谷杂粮的认知,更是远超普通农家孩子。她依旧圆润可爱,
是周家坞公认的“福气娃娃”,只是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里,
偶尔会闪过与年龄不符的沉静思索。这天傍晚,夕阳给村子镀上一层暖金。
陶乐瑶挎着个小篮子,在村后山坡上摘野菊花——阿娘说晒干了可以装枕头芯子,能安神。
她的小胖手灵活地揪着金灿灿的小花,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儿歌。忽然,
山坡下靠近溪边那片乱石堆里,传来一阵压抑的、小兽般的呜咽声,还有几声粗鲁的呵斥。
“小叫花子!敢偷摸到我们这边来!找打!”“滚回你的破庙去!脏死了!
”陶乐瑶好奇地扒开一丛半人高的茅草往下看。只见溪边,村里几个半大不小的皮小子,
正围着一个蜷缩在地上的孩子拳打脚踢。那孩子看着比陶乐瑶大不了多少,
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身上的破布条几乎遮不住身体,沾满了泥污。他死死抱着头,一声不吭,
只有身体被打得缩成一团。陶乐瑶认得他。他是去年冬天不知从哪儿流浪到周家坞的,
住在村外那座塌了半边、漏风漏雨的破山神庙里。村里人都叫他“石头”,
因为他总是沉默得像块石头,眼神也像石头一样又冷又硬。他偶尔会出现在村子边缘,
捡些别人丢弃的烂菜叶、挖点野菜根充饥,从不敢靠近村民的房屋和田地。
眼看那几个皮小子越打越起劲,陶乐瑶心里一紧。她看看自己挎着的篮子,里面除了野菊花,
还有阿娘怕她饿着放进去的两块杂粮饼子,用干净的布包着。“喂!你们干啥打人!
”陶乐瑶鼓足勇气,从山坡上探出小脑袋,大声喊道,
圆润的小脸因为紧张和生气绷得紧紧的。几个皮小子吓了一跳,
抬头一看是周家那个有名的福气胖丫头,领头那个叫二牛的不耐烦地挥挥手:“周家丫头,
少管闲事!这小叫花子偷摸到这边想偷东西!”“我没有!”石头猛地抬起头,声音嘶哑,
黑瘦的小脸上满是倔强,嘴角破了,流着血,“我只是…想喝口水!
”他指着旁边清澈的小溪。“呸!谁信!”二牛啐了一口。陶乐瑶挎着篮子,
小心翼翼地走下坡,走到溪边。她没理那几个皮小子,径直走到石头面前。
石头警惕地看着她,身体绷得更紧,像只随时会扑咬的小狼崽。陶乐瑶蹲下身,
从篮子里拿出那个干净的布包,打开,露出里面两块黄澄澄、还带着点温热的杂粮饼子。
她拿起一块,递到石头面前,声音软糯糯的:“给,吃饼子。阿娘做的,可香了。
”她的小胖手白白嫩嫩,和石头那脏污干裂的手形成了刺眼的对比。石头愣住了,
黑沉沉的眼睛里满是难以置信,死死盯着那块饼子,又看看陶乐瑶圆润无害的脸。
周围那几个皮小子也愣住了,二牛嚷嚷道:“乐瑶!你傻啊!给他吃?他…”“他饿了!
”陶乐瑶转过头,小眉头皱着,带着点奶凶,“你们再打人,我就告诉我哥,告诉李阿公!
”她哥是读书人,李阿公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这些皮小子都怕。二牛几个互相看看,
悻悻地嘀咕了几句“多管闲事”,到底不敢真惹周家,一哄而散跑走了。
溪边只剩下陶乐瑶和石头。夕阳的余晖落在两人身上。石头依旧蜷着,没敢接那块饼子。
“拿着呀!”陶乐瑶又往前递了递,小脸上是纯粹的善意,“吃了就不饿了。阿娘说,
肚子饱了,身上就有力气!”石头犹豫了很久,久到陶乐瑶的小胳膊都举酸了。
他才飞快地伸出手,一把抓过那块饼子,像怕陶乐瑶反悔似的,猛地缩回手,紧紧攥着,
脏污的手指几乎要嵌进饼子里。他低着头,狼吞虎咽地啃起来,噎得直伸脖子,
也顾不上旁边就是溪水。陶乐瑶看他吃得急,又把另一块饼子也放到他脚边的石头上,
小声说:“这块也给你。”然后她站起身,挎起装着野菊花的小篮子,“我回家啦!你别怕,
他们再打你,你就跑,或者…或者来我家院子外面喊我,我叫乐瑶!”说完,她迈着小短腿,
一摇一晃地走上了山坡。石头猛地抬起头,嘴里塞满了饼子,腮帮子鼓鼓的,
黑亮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个圆润的、挎着小花篮的背影消失在坡顶的茅草丛后。
他低头看着手里剩下的小半块饼子,又看看脚边那块完整的饼子,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咕噜声。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像想起什么,飞快地爬到溪边,胡乱捧起水喝了几口,冲下嘴里的饼屑,
然后小心翼翼地捡起地上几颗滚落在石缝里的、熟透了的野树莓。那莓子红得发紫,
沾着点泥土。他用自己的破袖子使劲擦了擦,擦得莓子皮都快破了,才宝贝似的捧在手心。
第二天傍晚,陶乐瑶又在同一个时间挎着小篮子去摘野花。刚到山坡下那片熟悉的溪边,
一个小小的、脏兮兮的身影就从一块大石头后面猛地窜了出来,吓了陶乐瑶一跳。是石头。
他还是那么瘦小,头发像枯草,脸上有新的擦伤,但眼神似乎没那么冷了。
他挡在陶乐瑶面前,不说话,只是飞快地伸出手。黑瘦的手心摊开,
上面躺着几颗红得透亮、水灵灵的野树莓,洗得干干净净,一颗颗饱满可爱。“乐瑶,
”他声音干涩沙哑,带着一种奇异的紧张,“甜!”说完,他把莓子往陶乐瑶手里一塞,
也不等她反应,转身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飞快地跑回了乱石堆后面,不见了踪影。
陶乐瑶摊开小胖手,看着掌心那几颗带着溪水凉意的野莓。阳光透过薄薄的果皮,
映出里面细小的籽粒。
“博闻馆”照例在她眼前刷屏:树莓Rubus idaeus,蔷薇科悬钩子属。
富含维生素C、花青素、有机酸…甜度约7.2%… 她没理会那些数据,
捏起一颗放进嘴里,轻轻一咬。清甜的汁水瞬间在口中爆开,带着山林间最纯净的果香,
一丝恰到好处的微酸点缀其中,果然很甜。她看着石头消失的方向,圆圆的脸上,
两个小梨涡又悄悄地陷了下去。3 枇杷膏的秘密周家坞的后山,长着一大片野果子树,
种类繁多。每年初夏,金黄的果子挂满枝头,是村里孩子们难得的零嘴,
大人们也会摘些枇杷的果子回去,熬成粘稠微苦的枇杷膏,留着咳嗽时喝。时光荏苒,
这年枇杷刚泛黄,陶乐瑶挎着个小篮子跟着阿娘上山。刚到山坡,
就看见几个半大孩子围着枇杷树又叫又跳,却够不着高处的果子。树下,
一个黑瘦的身影正像猴子一样敏捷地攀在枝桠间,手里拿着根带钩的长竹竿,
小心地将一串串金黄的枇杷勾下来,递给树下仰头张望的孩子。是石头。
那个住在村外破山神庙里的小乞丐。他似乎比去年又高了一点,但依旧瘦得厉害,
穿着打满补丁的旧衣裤,露出的手臂和小腿线条紧实。他动作很稳,眼神专注,
抿着嘴不说话,只把勾下来的最大最饱满的枇杷串,递给树下喊得最欢的孩子。“石头哥!
这边!这边还有串大的!”有孩子指着头顶。石头抬头看了看,调整姿势,
竹竿稳稳地伸过去。“哎哟!小心点!别摔着!”赵金花看得心惊,忍不住喊了一声。
石头闻声低头,看到坡下的陶乐瑶和赵金花,动作顿了一下,黑沉沉的眼睛里没什么波澜,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又继续专注地勾果子。
阳光透过枝叶缝隙落在他汗湿的额角。陶乐瑶仰着小脸看。很快,石头从树上溜下来,
拍了拍身上的灰。树下拿到果子的孩子们一哄而散,嬉笑着跑开了,也没人跟他说声谢谢。
石头似乎习惯了,默默捡起地上散落的几颗被碰掉、摔破皮的枇杷,在破衣服上擦了擦。
他看了看坡下的陶乐瑶,犹豫了一下,走过来。走到陶乐瑶面前几步远,他停下,
摊开黑瘦的手心。上面躺着两颗刚刚擦过的、金黄油亮、几乎没什么瑕疵的大枇杷。“乐瑶,
”他声音有些干哑,眼神落在陶乐瑶挎着的小篮子上,又飞快移开,“甜。”说完,
他把枇杷往陶乐瑶空空的篮子里一放,不等陶乐瑶和阿娘反应,
转身就大步流星地朝山神庙的方向走了,背影很快消失在林间小道。
赵金花看着篮子里那两颗明显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大枇杷,又看看石头消失的方向,
叹了口气:“唉,也是个可怜孩子…心倒是不坏。”陶乐瑶拿起一颗枇杷,圆润饱满,
表皮光滑,带着阳光的温度。“博闻馆”尽职地分析着糖分、水分、维生素含量。
她剥开薄薄的皮,露出晶莹的果肉,咬了一口。清甜的汁水瞬间溢满口腔,果然很甜。
自那以后,每年枇杷熟时,石头总会出现在后山。他不再只是帮那些调皮孩子勾果子,
更多的是帮着村里手脚慢的老人或者家里男人不在的妇人摘枇杷。他动作利落,
爬树又快又稳,摘下的果子完好无损。他依旧沉默寡言,摘完果子,主人家若给点吃的喝的,
他就默默接下;若不给,他也从不开口讨要,拍拍身上的灰就走。偶尔,
他还会带一两个同样面黄肌瘦、但眼神怯生生的半大孩子一起来帮忙。村里人从最初的戒备,
到后来也渐渐习惯了这个时节出现的、像影子一样沉默干活的小石头。陶乐瑶发现,
石头每次帮她家摘完枇杷,总会“恰好”路过她家院子,
然后“顺手”把几颗最大最黄的果子放在门槛上,或者塞给正在院子里喂鸡的她。
陶乐瑶每次想跟他多说两句话,比如“石头哥你喝水不?”或者“石头哥你吃饭了吗?”,
他总是摇摇头,或者飞快地答一句“不渴”、“吃过了”,就低着头匆匆走开。
只有那双黑沉沉的眼睛,在接过陶乐瑶硬塞给他的一个热乎窝头时,会飞快地亮一下,
像划过的火星。日子一年年过去,周家坞的枇杷黄了又青,青了又黄。
陶乐瑶从一个圆滚滚的小胖妞,长成了个身量渐开、眉眼舒展的少女。
脸蛋依旧带着点可爱的圆润,皮肤是江南水乡养出的细腻白皙,一双杏眼黑亮有神,
笑起来时,颊边两个小梨涡甜得能醉人。在周家坞人眼里,她依旧是那个有福气的“乐瑶”,
只是这福气里,似乎又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灵秀劲儿。周家的日子,
也在她不动声色的“奇思妙想”和阿哥陶立安这个“挡箭牌”的支持下,
像那春日里抽条的柳枝,一天天丰盈起来。起因还是后山那片野枇杷林。枇杷熟时,
村里家家户户都会去摘些回来,生吃解馋,或是熬成黏糊糊、带着微苦的枇杷膏,
留着咳嗽时挖一勺冲水喝。陶乐瑶跟着阿娘熬过一次,
看着那黑乎乎、卖相不佳、味道也实在算不上好的膏体,
“博闻馆”就在脑子里疯狂刷屏分析苦味来源和熬制过程的营养损耗。她琢磨了几天,
趁着阿哥陶立安休沐在家,兄妹俩在油灯下“讨论”学问时,她“无意”中提起:“阿哥,
书上说‘药食同源’,那这枇杷膏,是不是也能做得更好吃些?我瞧阿娘熬得辛苦,
熬出来黑乎乎的,还苦,囡囡都不爱喝。”陶立安正翻着书,闻言笑道:“小丫头嘴还挺刁。
古方记载,枇杷叶、枇杷果肉、川贝、蜂蜜之类,确有润肺止咳之效。不过咱家这土法子,
确实粗糙了些。怎么,乐瑶有想法?”他对自己这个妹妹的“奇思妙想”早已习惯,
甚至有些欣赏。陶乐瑶眨巴着大眼睛,掰着手指头“天真”地说:“我想啊,
是不是叶子要挑嫩的、没虫眼的,洗干净了还得把背面的绒毛刷掉?果子嘛,
要熟透的、金黄的,核儿要去干净!熬的时候,火不能太大,得慢慢熬,
还要加…加多点甜甜的野蜂蜜?最后熬得稠稠的、亮亮的,像糖稀那样,闻着香,吃着甜,
囡囡才肯喝呀!”陶立安听得眼睛一亮,觉得妹妹说得竟很有几分道理,
比书上干巴巴的方子生动多了:“嗯!乐瑶聪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制药之理,也在于用心!待下次枇杷熟了,我们试试!
”于是第二年枇杷季,在陶立安的“指导”和陶乐瑶的“建议”下,赵金花带着一双儿女,
精心挑选枇杷叶和熟果,一丝不苟地清洗、去毛、剥核,
加入陶乐瑶“缠着”阿哥去镇上药铺买来的少量平价川贝粉,
又舍得多放了些自家在山上寻到的野蜂蜜。小火慢熬,耐心搅拌。最终熬出来的枇杷膏,
色泽金黄透亮如琥珀,质地细腻柔滑,清甜的果香混合着淡淡的药香和蜜香,沁人心脾,
入口更是甜润微凉,毫无苦涩。陶大壮试了一小勺,惊得瞪圆了眼:“他娘!
这…这还是枇杷膏?这比镇上百味斋的梨膏糖还好吃!”赵金花也喜不自胜。
陶乐瑶趁机“怂恿”:“阿娘,咱家后山那么多枇杷树呢!熬这么多自家也吃不完,
不如…让爹做些好看的小竹筒装着,托货郎张伯带到镇上去问问?万一能换点钱,
给阿哥买纸笔也好呀!”陶大壮的手艺正好派上用场。他精心劈了细竹,打磨光滑,
做成一个个小巧玲珑、带着天然竹香的圆筒,筒身还用刻刀浅浅雕了简单的枇杷果子图案,
质朴又别致。金黄的枇杷膏灌进去,用木塞封好口,再系上一小截红布条点缀。
货郎张伯常年走村串镇,眼光毒辣。他拿起一筒掂量掂量,拔开塞子闻了闻,
又小心地用指甲挑了一点点尝了尝,眼睛顿时亮了:“哎哟!周老弟!金花妹子!
你们家这是得了啥秘方了?好东西!真是好东西!这品相,这味道!
搁在镇上药铺和南货店里,绝对抢手!放心,包在我老张身上!”张伯果然没食言。
第一批二十筒枇杷膏带到镇上,没两天就卖光了,还带回了回头客的预订。
周家小小的院子里弥漫着枇杷膏甜润的香气,也第一次听到了铜钱叮当作响的悦耳声音。
赵金花数着钱,笑得合不拢嘴,直夸儿子读书明理,女儿有福气又心细。
陶立安则含笑看着妹妹,眼底带着了然和纵容。有了这第一桶金,陶乐瑶的心思更活了。
她“缠着”阿哥教她认更多字,看些讲各地风物、农桑百工的书。
在“博闻馆”强大的信息支撑下,结合书上的记载和本地实际,她又有了新点子。
她发现村里妇人们绣的帕子、做的鞋垫,针线活儿其实都不差,只是花样老旧,
配色也过于沉闷。她凭着记忆和“博闻馆”对色彩、图案的分析,
“央求”阿娘和相熟的婶子们尝试些新的配色和更灵动的花鸟小样。起初婶子们将信将疑,
但试过之后,发现用陶乐瑶说的嫩绿配鹅黄绣叶子,用浅粉配水红绣花瓣,
绣出来的花样果然鲜亮活泼了许多。货郎张伯再带走这些绣品,价格竟也能往上提一提。
网友评论
小编推荐
最新小说
最新资讯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