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桥镇的更夫刚敲过三更,苏青禾蜷缩在柴房的草堆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三天前她在灶房偷听到李氏跟牙婆的对话——"这丫头模样周正,身段也匀实,卖去春香楼能换二十两。
"李氏的算盘珠子拨得脆响,"她亲娘死得早,我养她十年,总不能白养。
"十年?
苏青禾喉咙发苦。
亲娘咽气时攥着她的手说"去求你李婶",可这十年里,她吃过的糠饼比白馍多,冬天的破棉袄里塞的是芦花,去年腊月替李氏摔碎一只碗,被拿烧火棍抽得半个月下不了床。
如今亲娘的牌位还供在堂屋,李氏却要把她卖进火坑。
后窗的月光漏进来,照见墙角那口装杂物的破木箱。
苏青禾摸出藏在箱底的粗布包袱——里头是两件补丁摞补丁的旧衫,半块硬得硌牙的锅盔,还有亲娘临终前塞给她的银锁片。
那是她唯一的依仗。
柴房的木门"吱呀"一声。
苏青禾浑身紧绷,却见李氏举着煤油灯站在门口,鬓角的银簪子晃得人眼晕:"青禾啊,明儿张媒婆领人来相看,你收拾精神些。
""相看?
"苏青禾声音发颤。
春香楼的老鸨她见过,涂着猩红嘴唇,说话时露出金牙,哪是"相看"良配的模样?
李氏的手突然掐住她的下巴:"装傻?
你娘咽气前求我照顾你,我供你吃穿十年,如今该你报恩了。
"她指甲陷进苏青禾的皮肉里,"明儿跟张妈妈走,省得我动粗。
"等李氏的脚步声远去,苏青禾摸到后窗的砖缝。
这柴房后窗她试过七次,今儿个终于抠松了两块砖。
夜风吹得她打了个寒颤,可比起明早被塞进马车的绝望,这点冷算什么?
她猫着腰穿过菜园,绕过堆着粪肥的土堆。
石桥镇的狗在远处叫,她听见自己心跳如擂鼓。
出了镇子二里地,回头望时,李家那栋青瓦白墙的屋子还亮着灯——李氏定是怕她跑了,特意留的"守夜灯"。
"抓住那小贱蹄子!
"一声暴喝惊得苏青禾差点栽进沟里。
她回头望去,李氏举着火把,身后跟着两个赤膊的壮汉,手里攥着麻绳。
"青禾!
你娘的棺材板还没凉透呢!
"李氏的尖嗓子刺破夜色,"你跑了让我怎么跟你死去的爹交代?
"苏青禾跑得肺都要炸了。
她从小干农活,腿上有力气,可那两个壮汉是李氏花五文钱雇的地痞,脚步越来越近。
前面是片黑黢黢的林子,她咬咬牙扎了进去——青凉山的林子她听人说过,里头有野兽,可总比被抓回去强。
树杈刮得她脸生疼,她不敢停,首到火把的光被枝叶完全挡住。
可等她扶着树干喘气时,才发现自己彻底迷了路。
天蒙蒙亮时,苏青禾倚在老槐树下发抖。
她没吃过早饭,包袱里的锅盔昨晚跑丢了,此刻喉咙干得像塞了把碎草。
露水打湿了裤脚,寒意顺着腿往上钻,她想起亲娘坟前的荒草,想起李氏骂她"赔钱货"时的嘴脸,眼泪突然掉下来。
"布谷——"一声鸟鸣惊得她抬头。
不是普通的布谷叫,尾音里带着点转调,像人在模仿。
苏青禾屏住呼吸,看见树后转出个身影:穿粗布短打,腰间别着猎刀,手里提着半只野兔,发梢沾着松针。
"你是?
"她声音发哑,往后缩了缩。
那人停住脚,挠了挠头:"我叫陈阿憨,住山腰的草屋。
"他眼睛亮得像山涧里的石子,"你蹲这儿一宿了吧?
我天没亮上山,看你脚印歪歪扭扭的,像是迷了路。
"苏青禾的手攥紧了衣襟。
这林子里的猎户她听说过,镇子上有人说他"憨",说他打猎打到兔子还会给兔子包扎伤口。
可现在——"给。
"陈阿憨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掀开时麦香混着点焦糊味飘出来,"昨儿烤的馍,还热乎。
"苏青禾的肚子"咕噜"叫了一声。
她盯着那半块馍,喉咙发紧。
陈阿憨却别过脸去,望着远处的山尖:"我娘说,出门在外的人最可怜。
你要是信不过我,就拿馍,我站远些。
"他真的往后退了三步,背对着她蹲下。
苏青禾咬了口馍,麦香混着点盐粒的咸,是她十年没尝过的热乎滋味。
"我...我叫苏青禾。
"她咽下最后一口馍,"我从镇子上逃出来的,婶母要把我卖进青楼。
"陈阿憨转过脸,眉峰皱成个疙瘩:"那你别回去。
"他指了指山梁,"我那草屋虽破,能遮雨。
我娘走得早,就我一个人,你要是愿意,先住下?
"苏青禾望着他。
他的短打补丁叠补丁,可洗得发白,猎刀的皮套擦得发亮。
他的眼睛里没有镇子上那些男人的贪婪,只有...单纯的关切。
"好。
"她轻声说。
两人刚走了半里地,山风里突然飘来犬吠。
陈阿憨的耳朵动了动,拉着苏青禾躲到岩石后。
"那小贱人肯定在林子里!
"李氏的声音尖得刺耳,"找!
找不着别想拿赏钱!
"苏青禾的血一下子凉了。
她看见林子里晃动的火把,听见狗爪子扒拉落叶的声响。
陈阿憨却突然笑了,从怀里摸出个竹哨,放在嘴边轻轻一吹——是刚才那布谷鸟的叫声。
"跟我走。
"他拉着苏青禾的手往山岩后钻,"我知道条小路,从悬崖边绕过去。
他们带着狗,走不快。
"苏青禾跟着他爬过满是青苔的石头,听着身后的人声越来越远。
山风掀起她的碎发,她望着陈阿憨宽厚的背影,突然觉得——或许这山林,才是她的活路。
而此刻的李氏还不知道,她追进林子的这一步,正把自己推进了命运的齿轮。
等她寻到那片老槐树下时,只看见半块沾着露水的馍,和两行往深山去的脚印。
"贱蹄子!
"她跺脚时,银簪子"叮"地掉在地上。
可没人注意到,在她脚边的落叶里,正躺着半枚泛着银光的锁片——那是苏青禾亲娘留下的,方才爬岩时从包袱里滑出来的。
这锁片,日后会成为揭开一段血案的关键。
但此刻,它正安静地躺在落叶里,等待着被某双手拾起。
而苏青禾跟着陈阿憨,己经望见了山腰那间草屋。
屋顶的炊烟正往天上飘,像根细长的线,系住了两个漂泊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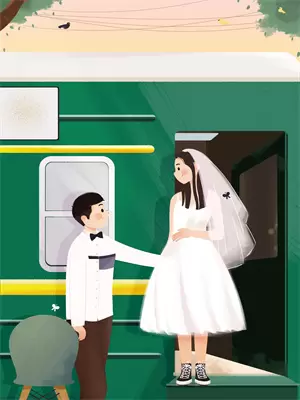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