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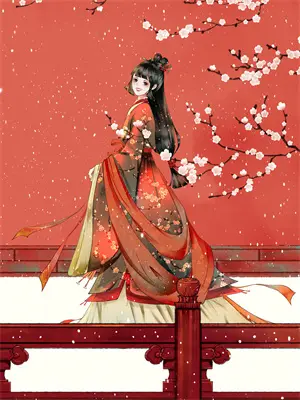
其它小说连载
小说《旧皮箱的流浪儿原唱》“拾壹州”的作品之沈念舟林知夏是书中的主要人全文精彩选节:第一楼里的时光胶囊2018 年深北京的风带着凉意穿过胡林知夏踩着外婆家阁楼那架吱呀作响的木楼梯往上走檐角那只铜铃被风撞得轻轻摇发出细碎又清脆的声像在诉说着被遗忘的往阳光透过积灰的老虎窗斜斜切进在满地堆放的旧藤箱、褪色的棉被和泛黄的书籍投下明暗交错的光空气中弥漫着樟木箱的木质香气与旧纸张的油墨味混合的气那是属于时光沉淀的味闻着就让人心生沉她是特地...
主角:沈念舟,林知夏 更新:2025-09-20 18:52:30
扫描二维码手机上阅读
第一章 阁楼里的时光胶囊2018 年深秋,北京的风带着凉意穿过胡同,
林知夏踩着外婆家阁楼那架吱呀作响的木楼梯往上走时,檐角那只铜铃被风撞得轻轻摇晃,
发出细碎又清脆的声响,像在诉说着被遗忘的往事。阳光透过积灰的老虎窗斜斜切进来,
在满地堆放的旧藤箱、褪色的棉被和泛黄的书籍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斑,
空气中弥漫着樟木箱的木质香气与旧纸张的油墨味混合的气息,那是属于时光沉淀的味道,
闻着就让人心生沉静。她是特地请假来帮外婆整理老物件的。上周三,
外婆在阳台晾晒那床盖了三十年的兰花被时,脚下一滑从竹梯上摔了下来,虽然只是骨折,
但医生反复叮嘱需卧床静养三个月,家里没人能腾出手,
清点阁楼杂物的事便落在了刚辞职的林知夏身上。这个阁楼她小时候常来,
那时外婆总踩着小板凳,从最顶层的樟木箱里翻出绣着海棠花的手帕,给跑得出汗的她擦脸,
手帕上的花香混着外婆身上的皂角味,是她童年最温暖的记忆。如今再踏进来,
熟悉的场景还在,却少了当年的热闹,只觉空荡又陌生。墙角堆叠的旧书旁,
一只深棕色的皮箱格外显眼。它不像其他杂物那样蒙着厚厚的灰尘,
只是表面的皮革因年月久远有些斑驳,露出底下浅棕色的底色,黄铜搭扣被摩挲得发亮,
泛着温润的光泽,四个箱角都用同色皮革仔细包边,针脚细密整齐,
看得出来当年主人对它的珍视。林知夏蹲下身,指尖轻轻拂过皮革上的纹路,
那触感粗糙却柔软,像是在触摸一段遥远的时光。忽然,
她的指尖触到箱盖内侧一张微微凸起的纸条,小心地掀开一看,是一张泛黄的牛皮纸,
上面用蓝黑钢笔写着娟秀的字迹:“赠砚舟,愿此箱载你所求,亦载归期。
—— 知夏”“知夏?” 林知夏心头猛地一震,指尖微微发颤。这是她的名字,从小到大,
家里人都这么叫她,可外婆从未提过,家里竟有位同名的长辈。她盯着那行字看了许久,
手指轻轻扣动黄铜搭扣,“咔嗒” 一声轻响,出乎意料,箱子没有上锁,
轻轻一掰便弹开了。箱内铺着一块靛蓝色的土布,布料摸起来厚实粗糙,边缘有些磨损,
却洗得干干净净。
土布上整齐地叠放着几件旧物:一本封面磨损得看不清书名的《唐诗三百首》,
书脊用棉线缝补过,能看到细密的针脚;一枚生了锈的铜哨,
哨口还残留着淡淡的铜绿;一张边缘微微卷曲的黑白照片,还有一叠用红绳系着的信笺,
红绳已经褪色,却依旧紧紧地捆着信笺。林知夏拿起照片,指尖不小心蹭到了照片边缘,
她连忙缩回手,像怕碰坏什么珍宝。照片里的年轻女子梳着齐耳短发,留着整齐的刘海,
穿着浅蓝色的学生装,领口系着白围巾,眉眼弯弯,嘴角带着浅浅的笑,那眉眼间的神态,
竟与自己有七分相似。她身旁站着个穿中山装的青年,身姿挺拔,头发梳得整齐,
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嘴角噙着温和的笑,两人并肩站在爬满青藤的旧式教学楼前,
身后的窗户里还能看到几个探头的学生,画面鲜活得像刚发生不久。林知夏翻到照片背面,
同样是那娟秀的字迹,用钢笔写着:“1957 年夏,于燕园未名湖畔。知夏与砚舟。
”她的心猛地一跳,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她连忙解开那根褪色的红绳,红绳在手指间绕了三圈,才把一叠厚厚的信笺松开。
抽出最上面的一封信,信封是浅灰色的,没有邮票,也没有地址,
只在正面用钢笔写着 “砚舟亲启”,落款是 “知夏”,
日期是 1958 年 3 月 12 日。林知夏深吸一口气,指尖捏着信封边缘,
小心翼翼地拆开。泛黄的信纸上,娟秀的字迹跃然眼前,墨水有些晕开,
却依旧清晰:“砚舟:见字如面。今日燕园的桃花开了,从宿舍到图书馆的路上,粉白一片,
如云似霞,风一吹,花瓣就落在肩头,像你去年给我摘的那朵。我站在桃树下,
忽然想起去年今日,你也是这样站在桃树下,手里拿着一本诗集,给我读你写的诗。你说,
‘桃花不及卿,一笑胜春朝’。那时我还笑你,说你写的诗太过直白,没有文人的含蓄,
你却挠着头说,心里想的就是这样,装不出含蓄。可如今想来,
却觉得那是我听过最美的情话……”信里满是对远方人的思念,
提及燕园的桃花、初遇的图书馆、一起排队打饭的食堂,
还有两人约定毕业后一起去江南的理想,字里行间藏着炽热的爱意与牵挂。
林知夏逐字逐句地读着,眼眶不知不觉就湿润了,泪水滴在信纸上,晕开了细小的墨点。
她放下信纸,心里满是疑问:照片里的 “知夏” 到底是谁?她和自己是什么关系?
“砚舟” 又去了何方?这箱信件为何会留在外婆家的阁楼里?
第二章 外婆的秘密当天下午,林知夏抱着旧皮箱回到自己的公寓。公寓不大,
客厅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她把皮箱放在书桌中央,将信笺一张张展开,整齐地摆放在桌面上,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信纸上,那些娟秀的字迹仿佛活了过来。她从下午读到傍晚,
直到窗外的天渐渐暗下来,才把所有信笺读完。从信中可知,
“知夏” 与 “砚舟” 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知夏” 学的是中国语言文学系,
“砚舟” 学的是历史系。1956 年 9 月,两人在图书馆初遇,
“知夏” 找一本《牡丹亭》找了许久,是 “砚舟” 主动上前,
递过那本藏在角落书架上的书;1957 年 5 月,在文学社的活动上,
“砚舟” 当着所有人的面,给 “知夏” 读了一首自己写的诗,
两人就此确定恋爱关系;1958 年初,国家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到基层去,
“砚舟” 主动报名去西北,参与当地的文化建设工作,“知夏” 原本也想一起去,
可外婆当时生了场重病,需要人照顾,她只能留在北京。前期的信件里,
满是生活琐事与甜蜜的思念:“砚舟” 会在信里描述西北的壮丽风光,
说戈壁滩的日落像火烧一样,
说当地百姓给他们送的馍馍带着麦香;“知夏” 会分享学校的趣事,
说文学社新来了个喜欢写现代诗的学弟,说食堂新出的南瓜粥很好喝,还会写外婆的近况,
说外婆能下床走路了,还念叨着要给 “砚舟” 做他爱吃的酱菜。
可从 1960 年开始,信件的内容渐渐变得沉重。“砚舟” 在信里说,
当地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短缺,每天只能喝两碗稀粥,地里的庄稼都枯死了,
百姓们饿得面黄肌瘦;他还说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半夜咳嗽,眼睛也因为风沙的侵袭,
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连写字都要凑得很近;“知夏” 的信里,也满是担忧,
她说自己多次向学校申请去西北,可每次都被拒绝,理由是她是独女,
需要照顾老人;她还说外婆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经常咳嗽,夜里睡不好,
却总叮嘱她不要告诉 “砚舟”,怕他担心。1962 年 4 月的一封信,
彻底击垮了 “知夏”。那封信的信封是陌生的牛皮纸,
字迹也不是 “砚舟” 熟悉的笔体,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纸条,
上面用打印体写着:“沈砚舟同志于 1962 年 3 月 15 日因积劳成疾,
不幸病逝。望节哀。” 纸条的下方,还附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
照片里的 “砚舟” 比之前瘦了很多,脸色苍白,颧骨突出,可眼神却依旧坚定,
穿着那件熟悉的中山装,背景是敦煌莫高窟的洞窟入口。林知夏拿着照片,
仿佛能看见 “知夏” 收到信时,双手颤抖、泪流满面的样子,那种绝望,
隔着半个多世纪,依旧能让人感同身受。最后一封信读完时,窗外已经完全黑了,
林知夏的脸上满是泪水。她拿起那本《唐诗三百首》,轻轻翻开,
忽然从书页间掉出一张干枯的银杏叶书签。书签已经泛黄发脆,
上面用钢笔写着两句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落款是 “砚舟赠知夏,
1957 年秋”。林知夏把书签贴在胸口,
仿佛能感受到当年 “知夏” 收到这份礼物时的喜悦。第二天一早,
林知夏带着旧皮箱去了外婆家。外婆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盖着厚厚的毛毯,
手里拿着一本旧相册翻看。看到林知夏进来,外婆连忙放下相册,笑着招呼:“知夏回来啦,
快坐,早饭在厨房温着,是你爱吃的豆浆油条。”林知夏把旧皮箱放在茶几上,
在外婆身边坐下,轻声说:“外婆,我昨天在阁楼里找到了这个箱子,
里面有一些信件和照片,您看您认识吗?”外婆的目光落在箱子上,
原本带着笑意的眼神忽然变得复杂,有惊讶,有怀念,还有一丝淡淡的忧伤。
她伸出颤抖的手,指尖轻轻抚摸着箱子的皮革,动作缓慢而轻柔,
像是在抚摸一件珍贵的宝物。许久,她才开口,
声音有些沙哑:“这是…… 你太外婆的箱子。”“太外婆?” 林知夏愣住了,
她从未听过外婆提起太外婆,“您是说,照片上的那个‘知夏’,是我的太外婆?
”外婆点了点头,眼眶渐渐湿润,她拿起桌上的纸巾擦了擦眼角:“是啊,她是你的太外婆,
也叫林知夏。那个男青年,是你的太外公,沈砚舟。当年你太外公去西北之后,
你太外婆每天都坐在窗边等他的信,有时候一封信能读上十几遍,夜里做梦都在喊他的名字。
可没想到,最后等来的却是他的死讯。你太外婆得知消息后,大病了一场,高烧不退,
差点就活不下去了。后来,看到我哭得不行,她才慢慢振作起来,说要好好活着,把我养大。
”外婆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你太外婆这辈子,从来没有再提过你太外公的名字,
也没有再看过这些信件和照片。她把这个箱子锁在阁楼最里面,还叮嘱我,
以后不要轻易打开。直到她去世的前一天,意识都模糊了,才拉着我的手说,她这一辈子,
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和你太外公好好告别,
没有跟他说一句‘我等你’;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你太外公,和他在燕园度过的那些日子,
是她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外婆握住林知夏的手,眼神里满是期盼:“所以,
我给你取名叫林知夏,就是希望你能像你太外婆一样,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
不留下遗憾;也希望你能比她幸运,能和自己心爱的人长相厮守,不用承受分离的痛苦。
”林知夏紧紧握住外婆的手,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两人交握的手上:“外婆,
谢谢您告诉我这些。太外婆和太外公的爱情故事真的很感人,我会好好珍藏这些信件和照片,
也会像太外婆一样,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第三章 档案馆里的往事自从知道了太外婆和太外公的故事后,
林知夏的心里总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她迫切地想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事情,
想了解他们在燕园的生活,想知道太外公在敦煌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
她查了北京大学档案馆的开放时间,准备去那里寻找更多线索。
北京大学档案馆位于校园的西北角,是一座灰砖红窗的古色古香的建筑,
门口挂着一块木质牌匾,上面写着 “北京大学档案馆” 六个烫金大字。
林知夏走进档案馆时,里面很安静,只有工作人员敲击键盘的声音和翻找资料的细微声响。
她向接待处的工作人员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工作人员很热情,让她填写了一张申请单,
然后带着她去了资料查阅室。查阅室里摆着几排长长的桌子,桌子上放着电脑和放大镜,
墙上挂着北京大学不同时期的校史照片。工作人员根据林知夏提供的名字和时间,
很快就在电脑里找到了相关的档案记录。“沈砚舟,1935 年出生,
1954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 年毕业,在校期间成绩优异,
多次获得校级奖学金,
发表过《唐代敦煌壁画的艺术特色》《敦煌文书中的历史信息》等论文,
毕业后主动申请赴甘肃敦煌,参与莫高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
” 工作人员一边念着档案内容,一边把打印出来的资料递给林知夏。林知夏接过资料,
手指轻轻拂过纸上 “沈砚舟” 三个字,心里满是激动。她仔细地读着资料上的每一句话,
太外公当年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在文学社里和同学们讨论问题的场景,
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形象,仿佛就在眼前。接着,
工作人员又找到了林知夏太外婆的档案:“林知夏,1936 年出生,
1956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入学成绩优异,语文和历史科目均为满分,
在校期间加入学校文学社,发表过《燕园的春天》《未名湖畔的思念》等散文和诗歌,
1960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因照顾老人辞职。” 看到太外婆的资料,
林知夏更加兴奋了,原来太外婆毕业后还留校教过书,
她之前从信里只知道太外婆在学校工作,却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职位。除了这些档案资料,
工作人员还帮林知夏找到了一些当年的校刊和报纸。
1957 年第 5 期的《北大周刊》上,
有一篇题为《燕园金童玉女:沈砚舟与林知夏》的报道,
报道中不仅介绍了两人的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
还详细描述了他们的爱情故事:“沈砚舟与林知夏,一个是历史系的才子,
一个是中文系的佳人,两人因书相识,因诗相恋,在燕园的未名湖畔、博雅塔下,
总能看到他们并肩散步的身影。他们不仅自己成绩优异,还经常帮助同学补习功课,
是同学们眼中的模范情侣。” 报道旁边还配了一张两人的合影,
和林知夏从旧皮箱里找到的那张照片是同一张,只是这张照片保存得更好,没有那么多磨损。
1958 年 2 月的《北京日报》上,
有一篇关于北京大学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赴基层工作的报道,
其中就提到了沈砚舟:“我校历史系毕业生沈砚舟同志,
在得知国家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后,第一时间报名参加,
他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敦煌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去保护,
我愿意用自己的知识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努力工作,
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看着这些资料,林知夏的心里充满了敬佩。
她仿佛能看到太外公当年在毕业典礼上,坚定地说出这番话时的样子,
也能感受到太外婆站在人群中,看着太外公远去的背影,既骄傲又不舍的心情。
从档案馆出来后,林知夏沿着校园的小路慢慢走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未名湖畔。
此时已是深秋,湖边的柳树叶子已经泛黄,随风轻轻摇曳,落下的叶子飘在湖面上,
像一只只小船。林知夏沿着湖边慢慢走着,
太外婆和太外公当年在这里散步、聊天的场景 —— 或许太外公曾在这里给太外婆读过诗,
太外婆曾靠着太外公的肩膀,指着湖面的鸳鸯说 “你看它们多好,永远不分开”。
一阵风吹过,带着湖水的凉意,林知夏裹紧了身上的外套,却觉得心里暖暖的,
仿佛那段遥远的时光,正通过这些细微的场景,与自己产生着奇妙的连接。
她走到湖边的一张长椅旁坐下,长椅是木质的,表面被岁月磨得光滑。她摸着长椅的扶手,
忽然注意到扶手内侧刻着两个小小的字 ——“知夏” 与 “砚舟”,字迹已经有些模糊,
却依旧能辨认出来。林知夏的心跳瞬间加速,她凑近了仔细看,确认那就是两人的名字,
旁边还刻着一个小小的爱心。原来,太外婆和太外公当年,
也曾在这里留下过属于他们的印记。她坐在长椅上,拿出手机,对着那两个字拍了张照片,
又抬头看了看远处的博雅塔。阳光洒在塔身上,给塔身镀上了一层金色,美得像一幅画。
她忽然觉得,自己此行没有白来,不仅找到了更多关于太外婆和太外公的资料,
还感受到了他们当年的爱意,这种感觉,比任何文字资料都更让她动容。
第四章 跨越时空的相遇就在林知夏沉浸在思绪中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刮过,
她搭在肩上的米白色围巾被风吹得飞了起来,打着旋儿飘向湖面。“我的围巾!
” 林知夏惊呼一声,连忙站起身去追,可围巾已经落在了湖面上,随着水波慢慢漂向湖心。
她急得团团转,湖边没有打捞工具,眼看围巾就要漂得更远,她只能沿着湖边小跑,
心里满是懊恼 —— 这条围巾是妈妈生前给她织的,对她来说意义非凡。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藏青色外套的男生快步从旁边的小路上跑了过来。他个子很高,身形挺拔,
头发有些凌乱,却挡不住眉眼间的清秀。他看到湖面上的围巾,又看了看焦急的林知夏,
没有丝毫犹豫,脱下外套随手扔在长椅上,卷起裤腿,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湖里。湖水很凉,
深秋的水温刺骨,男生却像是没感觉到一样,快速朝着围巾的方向走去。
他的鞋子踩在湖底的淤泥里,发出 “咕叽” 的声响,裤腿很快就被湖水打湿,
紧紧地贴在腿上。他伸手抓住围巾,又快步走回岸边,上岸时,身上的衣服已经湿透,
头发上还滴着水,水珠顺着脸颊滑落,落在下巴上。“同学,你的围巾。
” 男生走到林知夏面前,把围巾递了过去,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声音清澈,像山间的泉水。
林知夏接过围巾,围巾上还带着湖水的凉意,她却觉得心里暖暖的。
她看着男生浑身湿透的样子,心里满是过意不去:“真是太谢谢你了!你的衣服都湿透了,
这么冷的天,会不会感冒啊?要不我带你去我宿舍换件衣服?
或者我把你的衣服洗干净了再还给你?”男生摆了摆手,笑着说:“不用这么麻烦,
我家就在这附近,走路十分钟就到了,回去换件衣服就行。你没事就好,
这条围巾看起来对你很重要。”“对我特别重要,这是我妈妈织的。” 林知夏小声说,
又抬头看向男生,“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你,要不我请你吃饭吧?
就当是谢谢你帮我捞围巾了。”男生犹豫了一下,看着林知夏真诚的眼神,
点了点头:“那好吧,不过不用太破费,简单吃点就行。我叫沈念舟,你呢?
”“我叫林知夏。”“林知夏?” 沈念舟听到这个名字,愣了一下,眼睛微微睁大,
“这个名字…… 和我太奶奶的名字一样。我太奶奶也叫林知夏,
是 1950 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林知夏听到这话,也愣住了,
手里的围巾差点掉在地上:“你太奶奶也叫林知夏?还是北大中文系的?那你太爷爷呢?
他叫什么名字?”“我太爷爷叫沈砚舟,是北大历史系的,1958 年毕业后去了西北,
好像是去敦煌做文物保护工作了,后来就再也没回来。” 沈念舟一边说,一边挠了挠头,
“我奶奶说,太爷爷和太奶奶是燕园里的情侣,感情特别好,可惜后来分开了。
”林知夏的心跳瞬间加速,像擂鼓一样,她紧紧抓住围巾,
声音有些颤抖:“你…… 你有你太爷爷和太奶奶的照片吗?我这里有一张,
网友评论
小编推荐
最新小说
最新资讯
最新评论